中文学人系列专访27
斯文鼎盛,世运新潮。今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,为了回看北大中文系的发展变迁,重温几代学人的身姿与风采,共同探索和创造中文人的未来,我们策划了中文学人系列主题专访“我与中文系”。参与专访的学人中,既有白发满鬓仍心系学科的老先生,也有忙碌在讲台与书桌之间的中青年教师。他们讲述着人生道路上的岔路与选择,诠释着个人与世界之间具体而微的密切关联;他们梳理着治学过程中的难关与灵感,传递着朴素坚韧的中文传统。这是中文学人的一次回顾、总结和反思之旅,沿着先生们学术与理想的历史轨迹,我们得以触摸“活的历史”,感受“真的精神”。更多专访将陆续推出,敬请期待。
受访人:李宗焜
采访人:马尚、王可心
采访时间:2020年9月24日

图一:访谈现场,李宗焜在篆刻印章
受访人介绍:
李宗焜,1960年生,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,获博士学位。2017年9月起任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主要从事甲骨学与古文字学教学与研究工作。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北京大学藏甲骨整理、保护与研究”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“《甲骨文字编》修订与增补”。著有《甲骨文字编》(获“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”一等奖、第二届“李学勤中国古史研究奖”一等奖、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)、《唐写本说文解字辑存》《殷墟甲骨文字表》(博士论文)等。业余从事书法、篆刻的研究和创作。
采访人介绍:
马尚,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古文字方向博士研究生在读。
王可心,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古文字方向博士研究生在读。
马尚:老师好,今年是中文系110周年系庆,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。您博士是在北大中文系就读的,2017年又回到这里任教,是怎样的契机促成了您和北大中文系的这段学缘呢?
李宗焜:现在谈当年怎么考虑到北大读书,都已经是30年前的事,有点像“白头宫娥话天宝遗事”了。不过我当年的经历还是挺特殊的,似乎也值得提出来,当作一种历史见证。
我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都在台大读。但研究生还没毕业,指导教授就提前退休了,这不仅关系到我硕士论文的完成,也牵涉到下一个阶段该怎么办?我硕士论文写的是于省吾先生《甲骨文字释林》的研究。因为这个题目的关系,我跟吉林大学的林澐教授有比较多的联系,他是我接触的第一个中国大陆学者。那个时候两岸的互动还是很稀奇的,这是一段挺特殊的经历。硕士毕业的时候,连带一个问题是考博,我跟林先生讨论到这件事,最后林先生跟我说:“你去北大找裘先生吧!”就这样,我踏上了去北大的征程。

图二:1991年,李宗焜来北大读博不久时留影
1990年,我第一次到北京来。到北大,拜访了裘锡圭先生,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中国大陆学者。我把硕士论文呈请裘先生指正,并说明希望报考的来意。接着我去了吉林大学几天。再回北大时,裘先生对我的论文只说了一句话:“路子是对的。”同意我报考他的博士生。那时还有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,台湾根本不承认大陆的学历,裘先生也比较关心这个问题。学历不承认,你怎么办?我说,我要学到本事,不考虑学历承认的问题。后来幸运地考上了,当时的准考证、录取通知书,我现在还留着。
1994年初,我博三的尾声,史语所让我先用台大硕士回去任职。我跟裘先生商量。裘先生认为,我的题目体量这么大,短期内很难完成,他支持我先回史语所工作,同时抓紧时间把博士论文完成。当时的博士一般只读三年,因此向学校申请延长了一年。那个年代,延长年限是很特殊的例子,因为在延长期间,所有的公费都没了,也没宿舍,一般学生的经济能力都不好,几乎没有人敢延期;而我其实是回家,情况还好。就这样,我先回史语所工作,1995年再回来答辩,并取得博士学位。我应该是第一个从北大校长手上接过博士学位证书的台湾地区学生。
从1994年开始,我一直在史语所工作。2016年10月,我到长沙领取“致敬国学”的优秀成果奖,在颁奖会场上,复旦大学的汪少华教授跟北大中文系的廖可斌教授来找我。此前我跟汪老师是旧识,跟廖老师则素昧平生。廖老师跟我提到北大需要古文字学、甲骨学的老师,说我是北大毕业的,应该回来帮忙,力邀我加盟北京大学。我当时跟廖老师说,我要到2017年3月底,才具备退休的资格,现在恐怕无法考虑这个问题。廖老师说:“那正好,我们可以等。”此后,廖老师积极跟各方联系,我也想到:我是北大毕业的,北大有需要,我也应该回馈母校。而且,我对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”是有期待的。就这样,因缘际会,我又回到北大。
事后,每当有人问我为什么到北大,我都一言以蔽之说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来”。事实上,这真是我来北大的背景,也希望它可以发展为前景。

图三:1995年,李宗焜博士毕业
马尚:相比于您曾就读或工作过的台大、史语所,北大中文系给您留下了哪些不同的印象?
李宗焜:我在台大跟北大都当过学生,也都当过老师。我到北大读书的时候,就经常有人问我,北大跟台大有什么不同?我回答“北大比较大”。因为每个人的感受可能都不一样。
北大中文系分很多个教研室,学生的分流很明显;台大则打成一片,学生兴趣的不同,完全从选课中自我实现。另一个主要的不同,台大把文字、声韵、训诂列为全系的必修课,任何人(包括外籍生)都必须通过才能毕业;北大则即使三古都不是非修不可。任何做法都有它的考虑,不必加以轩轾,但我还是比较认同台大的做法(台湾很多重点大学也是这样做的),这绝不是本位主义或卖瓜的说瓜甜,而是所谓的“当行本色”。假使某人有一个篆书对联认不得字,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问中文系的人,如果我们跟他一样渺若天书,我们的专业训练在哪里?姑且不谈高深的研究,起码的专业认识还是要有的。
史语所跟大学明显不同。史语所是研究单位,它没有学生,也不需要上课,这是工作性质的差异。我以前先入为主地(或说莫名其妙地),很不喜欢教书,也许是墨菲定律,临老反倒成了教师。教书后才发现,其实也没那么讨厌,也真正体会到教学相长。面对学生各种各样的问题,也在鞭策自己进步。
但是,对我来说,差别最大的是心理的感受。在史语所,后面进来的人不管多么年轻,都会跟着我们一起变老。但是在北大,我们所面对的,永远是20岁上下的孩子,只有我在变老。这让我想到佛经里的“舟行岸移”。他们随时绽放着青春的魅力,鼓舞着我们心态上要保持年轻。

图四:1967年,李宗焜生平第一张照片
马尚:今年北京大学的古文字学被列入“强基计划”,目前的招生情况和教学安排有何进展?您认为北大古文字的学科优势是什么?您对北大古文字学的未来有什么期待?
李宗焜:“强基计划”是今年新推出的政策。目前招生已经完成,教学计划也有一些初步的安排。计划在进行规划和推动时,因为疫情的关系,我没能在学校,只能通过网路协助。具体的情况宋亚云老师比较了解。
我觉得北大中文系要推展古文字的研究,它的优势是相关的学科比较齐全。中文系重视古文献、古汉语,还有文字、声韵、训诂等专门课程。此外,历史系,甚至考古系相关的课程,对古文字的研究都有很大的帮助。我想这是北大中文系发展古文字学的一个优势。
国家既然出台古文字学“强基计划”这样的政策,我希望我们可以把握这个机会,把北大的古文字学队伍建立起来。希望有更多的同学对古文字学有兴趣,从而进入古文字学研究的行列。希望增强师资力量,让甲骨学、金文、简帛学,甚至古玺印学等古文字学重要的领域,都能有学有专精的老师来带领。希望经过大家的努力,北大中文系的古文字学队伍,能够慢慢壮大起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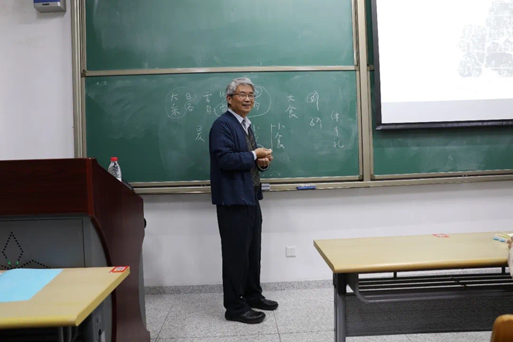
图五:2020年10月,李宗焜为20级强基计划的同学带来强基班第一堂课
马尚: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日益繁荣的今天,如何看待古典文献专业的发展方向?
李宗焜:不可否认,出土文献跟古文字的新材料,是现在的一个显学,受到学术界高度的重视。当然,在出土文献非常繁荣的今天,古典文献的价值,并不会因此而减损。现在非常新颖的出土文献,再过若干年,它也会变成古典文献。而古典文献虽然不是现在出土,但是它流传有序,曾经也是非常新颖的文献,并不会因为现在有了出土文献,减损其价值。事实上,很多出土文献跟古文字的研究,正是因为在古典文献上有比较好的基础,或是得到古典文献的印证才取得成果。这两者应该相辅相成。
另一方面,在出土文献这么繁荣的今天,我们对古典文献也应该有新的认识,而不是只局限于文献本身,应该充分与出土文献互相印证,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比过去学者得天独厚的优势。不管主力在出土文献或古典文献,只有偏重的问题,没有偏废的权利。

图六:访谈现场,李宗焜老师篆刻印章
马尚:古文字学素以“冷门绝学”见称,“周诰殷盘,佶屈聱牙”,是怎样的机缘让您当初选择了古文字学?除此之外,您还对哪些方向有过兴趣?
李宗焜:在中学时代,我读的比较多的其实是古文和诗词。到进入大学之后,对这一类的课程还是比较感兴趣的。这里提一下“当年勇”,在台大时参加古文、诗、词的比赛,三项都拿了第一。当然,以后我就不好意思再参加了。后来上了文字学、声韵学,还去旁听研究生的甲骨学,觉得也是蛮有趣的。当时台大中文系的学生,形容文字学跟声韵学加起来是一把剪刀,因为这两个学科往往有一半的学生挂科。中文系的学生,对这一类小学课程都非常地害怕。
其实,不管文学或小学,我都很有兴趣。但是,当时不自量力地认为,就是要“大胆担大担”,有种要把冷门绝学承担起来的使命感。当时的一点年少轻狂,决定了我未来的学术走向。像习主席所说的,要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,我不知道我第一粒扣子是不是扣对了,但是,就这样一路走来。
我的兴趣是比较广泛的。即使在学术上,我也不是只对古文字有兴趣,除了章回小说没有时间去读之外,唐宋以前的东西我都很喜欢。此外,我对艺术也很有兴趣,书法、篆刻都玩,当然这跟古文字学关系还是很密切的,我把古文字材料用书法、篆刻表现出来,让学术与艺术结合,自以为是地自得其乐。我还曾经疯狂搞过黑白摄影的暗房,玩得不亦乐乎,这当然跟学术领域完全不相干了。记得《幽梦影》里提到“人不可以无癖”,总要有一点专业以外的乐趣,人生会比较有趣一点。

图七:访谈现场,李宗焜创作书法“法古开新”
马尚:您的《甲骨文字编》是当下最便于使用的甲骨学工具书了,您对目前甲骨工具书的出版有什么想法和期待?
李宗焜:由于国家的提倡,甲骨学好像突然之间变成显学,这对于学术的推进当然很有帮助。但是不管怎么说,这还是属于少数人的专家事业,不需要一窝蜂的人去凑热闹。普及跟推广当然非常重要,但给普罗大众的东西,更需要专业,绝不是普及的东西,就可以由外行的人随便写。
我想甲骨工具书,最好还是由少数学有专精的学者,认认真真地去把它做好,而不是由半路出家的人做一堆似是而非的东西。毕竟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,不是照猫画虎或者看图说故事能够做好的。要做就要有“不成功便成仁”的决心,这绝对是劳心劳力的漫漫长路。我的《甲骨文字编》前后花了20年,也是吃足苦头。现在大家都说这是“高冷”的学问,我对高冷的解释是“门槛高”“坐冷板凳”。十年寒窗是免不了的。
马尚:您在甲骨材料的整理工作上付出了很多心血,您对学界目前的甲骨整理方法有哪些自己的看法?
李宗焜:现在的甲骨整理,跟以前相比有非常大的进步。在技术上、观念上都有很大的进步。在甲骨发现之初,所谓的甲骨整理,多半只是把拓片做出来就算好了,有的甚至于为了节省空间,还把拓片中没有字的部分剪掉,现在看起来当然是非常幼稚的行为。
当时由于技术条件没有成熟,甲骨整理最多也就提供拓片,随着科技的发展,我们对甲骨的整理就有了新的要求。现在甲骨整理,比较好的起码应该有几个条件:一是高清的彩照,二是清晰而准确的拓本,三是相对正确的摹本,四是释文。由于数字化的飞快发展,如果还能提供数字检索,当然是更好的。

图八:李宗焜手持甲骨文材料
有很多甲骨的细节,只有通过实际整理甲骨实物才会发现,当然有这种机会的人不多。我最近因为整理河南博物馆旧藏的甲骨,做了一点缀合的工作,深深体会到用拓片缀合有相当的危险性。有些拓片缀合看起来天衣无缝,但是经过实物检验却是错的;相反的,有些拓片看起来无论如何不可能缀合,实物却可缀起来。这就是利用甲骨实物去做整理的一个优势。多数学者没有这样的条件,我们只能期待,有机会整理甲骨实物的人,能够给学术界提供更多的信息。由于对甲骨整理的更加全面,能够提供的信息更多,我相信将来对甲骨的研究,会有另一个境界。
去年甲骨文发现120周年,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。我在相关会议上曾经倡议,应该纂辑21世纪版的《甲骨文合集》。现在的技术条件,以及国家的财政能力,都比上世纪80年代要强得多。如果能够由国家层面来领导,把全国的甲骨(甚至包含藏在其他国家的甲骨),全部按照相同的规范,用最新的技术,全面地重新加以著录,这样的《甲骨文合集》,就是甲骨学21世纪的《四库全书》。希望我这个祝愿,有实现的一天。这对甲骨的学术研究,是非常重大的贡献。
王可心:古文字学作为具有很强交叉性质的学问,它要求学生要有怎样的视野?对有志于此的学生有怎样的建议呢?您作为这个方向的导师,您希望以什么方式来培养研究生?
李宗焜:我想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当年跟裘先生读书的时候他对我们的要求。我记得裘先生有一次跟我们谈话,他说首先是做人,我们人活着是为了做人,不是为了做学问,所以首先是做人,只有做人及格,做学问才有意义。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。另外有一次他提到说,你学问好,要让人家觉得是对他有帮助的,而不是让他觉得难堪。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。就是说,我们首先是来做人的,作为人的要求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人不好,其他东西越好,祸害越大。所以我觉得做人是最重要的。
讲到我们专业的做学问,我特别强调知识面一定要广,当然不能广得漫无边际连自己都抓不到。我当年跟裘先生读书的时候,有一次裘先生跟我说:“你也不能一天到晚搞甲骨,还是要休息。”我当时觉得很惊讶,难得裘先生还会关心我们要休息。但是你知道他后面讲什么吗(笑)?他说:“你也不能一天到晚搞甲骨,还是要休息,休息的时候看一下金文。”意思就是说你要孜孜不倦,根本不能懈怠。但是你一直都看甲骨,可能会疲乏,换个东西看,甲骨看累了,看一下金文。总之要高强度地学习,多方面地充实。以前裘先生也跟我们讲过,如果你只搞一种东西,搞不深。当然很惭愧,我们这一点都做得不够,但是这个说法肯定是对的。

图九:1988年中文系古文字专家裘锡圭在讲课
古文字学大概是所有学科里面需要相关知识最多的一门学问。唐兰先生说,古文字学的学问不在古文字学本身,这是非常有道理的。纯粹从文字论文字,它的局限性很大。很多古文字的认识,往往是通过和其它古文字材料或古文献互证。除了传世文献和文字学、声韵学等传统小学外,还要关注历史学、考古学、器物学中的相关知识。我一再说,知识面越广,所能解决的问题就越多。有一句唐诗说,“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”,不同的高度,会有不同的视野。怎么样更上一层楼呢?那只能靠自己不停地努力。学问的事,就是比气足、比气长。先秦典籍要尽可能多读,这些都是研究古文字学非常重要的资产。
我在课堂上一再跟学生讲,最好读书的时间就是当学生的时代,俗话说,“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”。你过了学生这个阶段,绝对不会再有像当学生这么好的读书机会,即使你有那样的机会,你的体力、记忆力各方面都不如当学生的年代。你进入了社会,即使有再好的环境让你读书,你的烦恼也会变多,绝对不像学生这么单纯。当学生唯一的工作就是念书,你没有其他需要烦恼的,而且当学生的时候又年轻,身体又好,记忆力也好,这个时候不努力,更待何时?
有一句话叫做“好(hǎo)读书,不好(hào)读书;好(hào)读书,不好(hǎo)读书”。你们现在属于好读书的阶段,不要不好读书。我们现在虽然很有体会,可惜现在是好读书,已经不好读书了,读了马上就忘。你们年轻,在保障身体健康的前提下,要抓住这个机会,一辈子只有一次,过了就没有了。

图十:李宗焜与采访人马尚(右一)、王可心(左二)及学生王悦(左一)合影
王可心:您是如何看待学术的,学术在您生命中的意义是什么?
李宗焜:学术是坐冷板凳的专家事业。要能耐得住寂寞,不追求名利,也不可能速成,甚至要不求回报,因为有些努力可能付出很多,最后毫无所得。所以要搞学术,首先必须要有兴趣,否则一辈子去做一件没有兴趣又没有名利的事,那真是太悲催了。学术需要全心全意地投入,甚至有人“一生唯一念”。我很惭愧没法做到这样。我的兴趣太多,都占了一些时间,美其名曰多才多艺,实际则是备多力分。但不管怎么说,从事学术工作二三十年了,人生有几个二三十年,人生中大部分的精华岁月,都投入学术工作,也算是生命的意义吧。

图十一:李宗焜为中文学子所刻印章:“闻健自修,分分己获”
责任编辑:席云帆
排版:李岚
图片来源:图一(吕宸摄)、五(来源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官微)、六(吕宸摄)、七(周昀摄)、十(徐梓岚摄)、十一(周昀摄)为原创,图二、三、四、八为受访者提供,图九来源于北京大学档案馆。